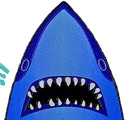文献:超越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美国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免疫安全技术委员会(ITC)对免疫调节剂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的综合方法
付永超 / 2026-02-03
原文链接:https://ascpt.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cpt.3316
原文作者:Mineo Matsumoto, Joseph Ryan Polli, Suresh K. Swaminathan, Kaushik Datta, Cris Kamperschroer, Marie C. Fortin, Smita Salian-Mehta, Rutwij Dave, Zheng Yang, Payal Arora, Masanori Hiura, Mizuho Suzuki, Frank R. Brennan and Jean Sathish
原文协议:CC BY-NC 4.0
译者注:主要由Edge浏览器自带的网页翻译功能翻译,译者额外校对了部分词汇的中文翻译比如“pharmacodynamics”在本文应翻译为“药物效应动力学”,而不是“药效学”,以及比如"首次人体(FIH)",“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最大耐受剂量(MTD)",“免疫调节剂(Immunomodulators)",“免疫刺激剂(immunostimulators)",“同类别首个(first-in-class)",“同类别下一个(next-in-class)",“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等。
抽象
在"首次人体(FIH)“临床试验中给予一种新型候选药物是药物开发的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阶段,对于"免疫调节剂(Immunomodulators)“尤其如此,因为免疫调节剂是一类具有广泛作用机制和相关安全风险的多样化和复杂的药物。“免疫刺激剂(immunostimulators)“的风险通常较大,免疫刺激剂的安全性问题与急性毒性相关,而"免疫抑制剂(immunosuppressors)“的风险与慢性效应相关。目前用于免疫刺激剂”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的方法主要集中在确定"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 minimum anticipated biological effect level)",这往往导致"亚治疗(sub-therapeutic)“剂量,导致长期和昂贵的"剂量递增(escalation)“阶段。“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Institute)“和"免疫安全技术委员会(ITC, Immuno-Safety Technical Committee)“组织了一个项目,通过两种互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i)对”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策略的行业调查和(ii)对肿瘤和非肿瘤适应证的免疫调节剂进行详细的案例研究。来自行业调查答复的关键信息强调了对更动态的"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方法的偏好,因为"体外实验(in vitro assays)“似乎不能代表免疫调节剂的真实生理状况。这些原则在案例研究中得到突出强调。为了解决上述主题,我们在"药物开发创新和质量国际联盟-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工作组(IQ MABEL Working Group, IQ MABEL工作组,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Innovation and Quality in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 minimum anticipated biological effect level Working Group)“的指导下,提出了一种修订后的决策树。这一方法有助于对免疫调节剂的”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提出更完善的建议,允许对其"作用机制(MOAs, mechanisms of action)“和相关的风险获益比等因素进行细致的考虑。
免疫调节涉及使用特定的药物或分子来操纵患者的免疫系统。这种操作旨在加强各种免疫相关疾病的治疗,包括癌症、感染和自身免疫/炎症条件。免疫调节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如"小分子药物(small molecule drugs)"、“单克隆抗体(mab, monoclonal antibodies)"、“重组蛋白(recombinant proteins)"(如"细胞因子(cytokines)"、“趋化因子(chemokines)"、“生长因子(growth factors)“等)、“寡核苷酸(oligonucleotides)"、“疫苗(vaccines)“以及"基因和细胞疗法(gene and cell therapies)"。
这些类型的分子可以大致分为两组,“免疫刺激剂(immunostimulators)“和"免疫抑制剂(immunosuppressors)"。免疫刺激剂是能够增强或激活免疫系统活性的治疗性实体。这些分子通过多种"作用机制(MOAs)“发挥作用,如促进免疫细胞的生成,增强其活性(如T细胞、NK细胞和巨噬细胞),或使其与靶细胞接触,从而实现激活和对靶细胞的直接、特异性杀伤。例如,重组细胞因子,如IL-2和GM-CSF可用于"修饰(modify)“免疫系统以达到预期效果,如刺激T细胞"增殖(expansion)“来增强对死肿瘤细胞的杀伤,或者促进中性粒细胞增殖以帮助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患者。小分子药物可用于激活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效应细胞,而"检查点抑制剂(checkpoint inhibitors)"、“共刺激激动剂(costimulatory agonists)“和"CD3双特异性单克隆抗体(CD3-engaging bispecific mAbs)“可激活T细胞,从而增强对肿瘤的杀伤作用。
相反,免疫抑制剂旨在"减弱(dampen)“或"阻碍(inhibit)“来抑制免疫系统的活动。这些药物主要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或防止移植排斥反应。免疫抑制剂通常针对特定细胞类型(例如自身反应性T细胞或B细胞),以降低其功能、消耗其功能或抑制这些细胞产生的"炎症介质(inflammatory mediators)"。最常见的一类免疫抑制剂是"糖皮质激素(corticosteroids)",其作用广泛,广泛用于治疗多种炎症性疾病。免疫抑制生物制剂的例子包括利妥昔单抗(rituximab),它可以在多种炎症性疾病中耗竭自身反应性B细胞;以及阿达木单抗(adalimumab),它是一种促炎性细胞因子TNFα的抗体,通过阻断TNFα用于减轻类风湿关节炎和克罗恩病全身性炎症反应。为了本手稿的目的,免疫刺激剂和免疫抑制剂被定义为在特定指征中分子的假定药理学活性。例如,具有"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 Antibody Dependent Cellular Cytotoxicity)“活性的抗体能够刺激免疫系统以促使自反应细胞被杀死,而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这会产生免疫抑制作用;因此,该分子被定义为一种免疫抑制剂。重要的是,尽管一些治疗手段最终可能是免疫抑制剂(正如其药理学所预期的那样),但在产生预期效果的过程中刺激了免疫系统,这并不一定会降低与此类分子相关的风险。
免疫调节剂药物会因过度的免疫"刺激(stimulation)“或"抑制(suppression)“而带来风险。虽然临床前试验通常评估药物的安全性并指导"首次人体试验(FIH)“剂量,但强效免疫刺激剂的出现使FIH剂量确定变得复杂。这是由于人和动物生理差异、免疫靶点表达低、免疫激活少以及标准动物模型缺乏相关疾病组织等原因造成的。此外,免疫刺激剂可以分类为功能亚组,如共刺激激动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PIs)和CD3双特异性和其他多特异性(图S1),每一种都需要对”首次人体(FIH)”剂量设置进行特定考虑。与靶向可溶性抗原的免疫调节剂相比,具有膜结合靶点的免疫调节剂具有更高的安全风险。
在"首次人体(FIH)“研究中,免疫抑制剂和免疫刺激剂的免疫介导毒性风险不同。设计用于抑制免疫系统的免疫抑制剂(例如,抑制T或B细胞或阻断可溶性细胞因子)在连续长期使用时会增加感染风险,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会因感染致癌病毒而增加癌症风险。然而,这些通常在”首次人体(FIH)”研究中没有观察到,且由于急性毒性风险较低,通常有理由提高起始剂量。相反,设计用于直接或间接激活免疫系统的免疫刺激剂有发生急性毒性(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和某些情况下"免疫细胞激活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 immune cell activation-rel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以及自身免疫的风险,这取决于"作用机制(MOA)",而这通常需要较低的”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2006年“TeGenero灾难(2006年TeGenero公司TGN1412药物”首次人体(FIH)”的大象人事件)“不幸地突出了免疫调节剂不适当的”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的潜在后果。这一事件促使采用"最小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 minimal anticipated biological effect level)“来确定安全的起始剂量。”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计算考虑了各种"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数据,如"靶点结合(target binding)"、“受体占用(RO, receptor occupancy)"、“暴露-反应(exposure-response)“分析以及相关动物物种在药理学剂量下的暴露情况。在”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中,对安全性的强调往往掩盖了对疗效的考虑,导致剂量设定保守且剂量递增(escalation)“时间较长。一些监管机构,如美国FDA,正对非”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策略更加开放,而非仅依赖最敏感的方法,以更快地达到"药理学活性剂量(pharmacologically active dose)",前提是优先考虑受试者的安全。在首次患者试验中坚持”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可能导致起始剂量极低,几乎没有潜在益处。虽然低起始剂量适合健康志愿者的”首次人体(FIH)”研究以评估初始药物代谢动力学特性,但对于首次患者试验(例如晚期癌症适应证)可能不合适,在这些试验中,患者可从更高剂量中获益。由于需要多个队列才能达到"药理学活性剂量(PAD, pharmacologically active dose)",因此延长了临床开发时间表,这可能会延迟对患者的益处,并增加开发成本。然而,在免疫调节”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方面,已发表的指南和实施之间仍然存在差距。
“药物开发创新和质量国际联盟(IQ Consortium, IQ联盟,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Innovation and Quality in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 )“此前基于对88种分子的行业调查发表了一篇论文来解决这个问题。申办方由于高风险及未知风险、“同类别首个分子(first-in-class molecules)"、激动剂作用模式以及用于安全性评估的相关动物物种,而常常选择”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然而,对于10个”首次人体(FIH)”提交的项目(即生物制品和小分子),”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被监管机构强制执行,尽管该方法最初并非由申办方提出。此外,在本次调查中,11种蛋白质治疗药物必须根据“卫生/健康行政部门(Health Authority)“的建议修改其策略,以实施较低的剂量,3种分子将其"首次人体(FIH)“剂量策略从非"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修改为"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相反,只有1个案例根据美国FDA建议确定了更高的剂量。拥有晚期数据的分子中约三分之一,“最大耐受剂量(MTD, maximum tolerated dose)"、“有效剂量(effective dose)“或"推荐的2期剂量(RP2D, recommended phase 2 dose)“是起始剂量的100倍以上。
“药物开发创新和质量国际联盟(IQ)“论文还概述了基于药理学和毒理学的”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方法,并提供了”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策略和”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使用时需要考虑的决策树和风险因素。提供了简短的案例研究,主要是为了帮助使用决策树来选择”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本文旨在通过提供更多详细的案例研究来扩展"药物开发创新和质量国际联盟(IQ)“论文,涵盖多种具有不同"作用机制(MOA)“的免疫调节剂,强调如何定量的考虑和整合来自体外和体内不同来源的药理学及毒理学研究的数据用于”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讨论了是否采用"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或基于不同风险因素建议提高起始剂量,以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Health Authority)“对这些决定的反应。还提供了基于不同制药申办方和"监管机构(regulatory agencies)“进行的免疫调节剂临床研究所得见解而修订后的综合决策树。这些发现将为免疫调节剂”首次人体(FIH)”剂量方法的选择提供参考。这项工作是由"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Institute)““免疫安全技术委员会(ITC, Immuno-Safety Technical Committee)“主导的项目活动之一。
调查信息
我们最初分析了 2001 年至 2022 年间 356 种免疫调节剂的公开数据(见补充信息 )。本研究旨在了解基于适应症和/或"作用机制(MOAs)“的”首次人体(FIH)”剂量设定方法的趋势。如图 1 所示,免疫调节剂分为两类:A 组,非肿瘤适应症如过敏或自身免疫疾病,主要使用免疫抑制剂,急性毒性风险较低;B 组,用于肿瘤适应症的药物,主要为免疫刺激剂,急性毒性风险较高。值得注意的是,”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成为肿瘤相关免疫调节剂(B 组)中”首次人体(FIH)”剂量设置的首选方法,尤其是针对所有 CD3 双特异性( 见图 1)。
图1目前工业上应用的”首次人体(FIH)”剂量策略总结。在总共356种免疫调节剂中,提取了55种产品(~15%)其”首次人体(FIH)”剂量设置方法是从公开信息中已知的。在这55种产品中,”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药理学活性剂量(PAD)”和"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方法的总体百分比在最上面的横条中显示。其中,A组和B组的”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药理学活性剂量(PAD)”和”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方法的百分比显示在中间的两个横条中。值得注意的是,”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是B组”首次人体(FIH)”剂量设定的明显优先方法。此外,在这些B组产品中,所有CD3双特异性抗体均选择了”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最下方的横条)。
在初步评估之后,我们调查了11家” HESI-ITC(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免疫安全技术委员会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Institute Immuno-Safety Technical Committee)“成员公司,以确定为各种类型的免疫调节剂建立”首次人体(FIH)”剂量的最佳实践。调查问题在补充信息和行业调查中有详细的描述;此外,表S1总结了这些公司的常见回答。我们还获得了关于”首次人体(FIH)”研究剂量递增阶段的意见,并在表S2中总结。
在我们对成员公司的调查中,主要表现为四个主题。这些包括(i)反对过度使用基于体外数据的”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ii)对体外系统过度的敏感且缺乏生理相关性的担忧,(iii)倡导”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的替代方法,如对较低风险产品的使用"PAD(药理学活性剂量, pharmacologically active dose)“方法,以及(iv)建议"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建模,或对"同类别下一个(next-in-class)“药物的"反向翻译(reverse translation)"(使用现有临床数据指导”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表S1)。关于这四个主题的更多细节,请参阅补充信息和调查回应——来自11家公司的共同回应。
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外,上述11家公司中有10家公司对我们的调查提供了额外的回复,其中包括作为其”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一部分的 RO 值(%)(图 2)以及 ECx(“有效浓度(effective concentration)")值(图 3)。定义体外”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的典型终点包括免疫细胞激活、细胞因子释放(“板结合和/或可溶性(plate-bound and/or soluble)")、靶标调节(杀死或激活)以及抗肿瘤反应/杀死(用于肿瘤学),其中选择"效应器(effector)"(E):“靶点(target)"(T)比例和与疾病适应症相关的检测设置的重要性经常被指出。基于细胞的药理学实验也被用于免疫抑制剂的体外”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一家公司回应称,由于缺乏相关物种的非临床毒性数据和先前临床经验,”首次人体(FIH)”剂量的设定依赖于利用体外实验的"效力值(potency values)"(EC20)以及预测的动物组织中靶浓度(图3,公司J)。
图2 受访公司在其用于免疫调节剂"首次人体(FIH)“剂量设定的”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指标(indices)“中,对调查问题给出的RO值(%)示例。在受访公司使用”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的情况下,总体上倾向于对高风险免疫调节剂使用低于RO50%的RO值,而对低风险产品使用高于RO50%的值。然而,在具体数值选择上存在一些差异。例如,一家公司(A)选择RO10%作为评估针对癌症或"严重致残或危及生命疾病(SDLT, severely debilitating or life-threatening diseases)“的激动剂或高风险分子的起始点,然后向更高值调整。两个公司则以RO20%作为起始值:其中一家公司(G)在评估具有良好表征平台的分子时将其向RO50%调整,另一家公司(C)则在尝试确定能够通过少量剂量递增步骤达到治疗范围的剂量时采用该值。两个公司(D和F)在评估免疫刺激剂时采用了低于RO50%的值范围。另一方面,用于评估免疫抑制剂的值范围高于RO50%的是两家公司(D和J),而对于同一产品类别,另一家公司(J)提出使用低于RO80%的值。在该图示例中,一家公司(H)用于评估没有安全问题的检查点抑制剂,异常地使用了高于90%的值,并且这是唯一部分采用体内”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而非体外方法的示例。请注意,该图中的发现已纳入图4(决策树)中,作为颜色标识的一部分。
/image-20260203220851166.png)
**图3 受访公司在其用于免疫调节剂"首次人体(FIH)“剂量设定的药理方法"指标(indices)“中,对调查问题提出的ECx(“有效浓度(effective concentration)")值(%)示例。**参与调查的公司在用于其”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淡红色区域)或”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淡蓝色区域)方法指标的ECx偏好值上存在差异。首先,对于体外或体内的”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4家公司(A、B、C、J和K)优先选择EC10作为向更高值(如EC20)推进的起点。一些公司(D、F、J和K)也显示了不同的值区间,例如EC20-EC30或EC20-EC50。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值区间用于高安全风险免疫刺激剂/激动剂的指标。一家公司(C)也使用EC20来确定可在少数剂量递增步骤中达到治疗范围的剂量。对于”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亦有一家公司(F)显示了EC50-EC80的值区间,但这是用于评估免疫抑制剂。在缺乏药理学相关模型的情况下,一家公司(J)提出了基于预测在靶组织浓度而非系统暴露的EC20值。一些公司还展示了相对低风险产品的”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的ECx值区间,其中一家公司(D)的例子是针对新靶点免疫抑制剂的EC30-EC50,而另外两家公司(A和/或D)的例子是针对具有一定临床先例靶点的免疫抑制剂的EC50-EC80。如预期的,”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的ECx总体值区间高于”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因此这两种方法可以在同一条连续线上进行区分,如本图所示,而不是在两条独立平行线上。请注意,该图中的发现也被纳入图4(决策树)作为彩色标尺,但在该图中位于“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和“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两个框的下方。
优化免疫调节剂“首次人体(FIH)”剂量设定的决策树
为了开发一种有效的免疫调节剂”首次人体(FIH)”剂量设定方法,我们调整了之前针对包含免疫调节剂的通用药品提出的决策树,修订后的决策树主要流程与 Leach 等人保持一致。该系统由三层体系组成:(i)基于作用机制、靶点药理学和/或临床经验的安全性风险,(ii)体外人源样品实验和/或毒理学动物物种的相关性,以及(iii)基于非临床毒理学研究的临床安全风险(图4)。
/image-20260203220809111.png)
图4 建议的决策树用于指导免疫调节生物制剂的"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 免疫调节剂"首次人体(FIH)“剂量设定的决策树始于基于产品作用机制及相关临床经验的风险预测。也就是说,决策树的初始问题是“免疫调节剂是否存在潜在的免疫安全风险?(树的第一层)。“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且第二层评估中判断该产品没有相关的体外人源样品实验和体内动物研究,则决策将导向”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即最保守的方法,会导致较低的"首次人体(FIH)“剂量;而如果第一层问题的答案是为“否”,并且仍然没有相关实验/研究,决策会导向”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即较不保守的方法。在其他情形中,决策还依赖于第三层评估,即如果非临床数据显示有任何安全性问题,决策倾向于采用”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如果没有,则可能采用较不保守的”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或”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方法。肿瘤产品的"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 Highest Non-Severely Toxic Dose)“和"10%动物出现严重毒性反应的剂量(STD10, Severely Toxic Dose in 10% of animals)“方法可归入与”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方法相同的决策框(*)。当决策进入”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尤其是体外数据时),“首次人体(FIH)“剂量可能通过"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计算(见图 3),其中"药物效应动力学(PD)“基于反映各产品相关安全风险的 RO 值(%)评估(见图 2)。 如果决策落入”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或”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首次人体(FIH)”剂量也可通过"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方法计算(见图3),此时"药物效应动力学(PD)“基于ECx(有效浓度)值(%)评估,同样反映每种产品的相关风险(见图3)。图中显示的RO或ECx值(%)在整个免疫调节剂相关安全风险范围内的排列,遵循了图 2 和图 3 中公司调查结果。在流程末端,针对”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药理学活性剂量(PAD)”和”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方法的所有情况,可适当应用安全系数以得出”首次人体(FIH)”剂量。”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药理学活性剂量(PAD)”和”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方法的选择、RO和ECx值(%)比例尺上的选择定位,以及安全系数(x、y和z)的应用,都可根据产品的风险/获益平衡及临床可监测性(黄色框)进行调整。
然而,我们大幅扩展了决策树的下半部分,特别是“退出(exit)“选项,其中Leach 等人包括“基于”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的和非”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的方法"以及“非”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的方法(例如”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相比之下,我们将这些方法分为“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和"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方法,后者包括针对肿瘤产品的”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和 “10%动物出现严重毒性反应的剂量(STD10)”方法。”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方法指的是使用毒理学数据而非药理学数据来选择"首次人体(FIH)“剂量。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对于毒性低的分子,毒理学研究中的”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很少被使用,因为它会导致起始剂量过高(例如根据 2005 年 FDA 指南,“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为100 mg/kg → “人体等效剂量(HED, Human Equivalent Dose)” 为 100 mg/kg→基于BSA为16.6 mg/kg→MRSD为10 mg/kg)。因此,会应用额外的安全系数,或采用"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建模(参见案例 1、3 和 4)。此外,我们为”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和”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下的 ECx 值以及”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下的 RO 值集成了刻度条。些刻度条来源于我们公司的调查结果,可作为免疫调节剂"首次人体(FIH)“剂量设置中药理学方法的参考标准(图 2 和图 3)。这一新布局旨在帮助用户不仅选择一个“退出(exit)“框,还能在框内微调其决策。最后一步是根据风险/获益和/或临床可监测性等因素,选择合适的安全系数以估算最佳"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 见图 4),这与 Leach 等人的原则相符。
行业案例
为了寻找用于推导精化决策树(图 S2–S8)的基础,并了解"首次人体(FIH)“剂量设定方法及免疫调节剂的最佳实践,我们请求 HESI-ITC 的成员公司提供扩展的案例。参与公司(表 1)提交了 14 个案例。在这 14 个案例中,我们优先选取了 7 个,这些案例与上述提出的四大主题吻合(表 S1),并对它们进行了进一步的描述和分析,如下所示。其余案例的简要描述见表 1。
表1 从工业界收集的案例摘要
| 产品 | 组别 | 免疫调节剂类别 | 靶点 | 作用机制 | 临床前研究 | 同类别首个(FIC)/同类别下一个(NIC) | 安全风险 | 首次人体(FIH)剂量 | 用于首次人体(FIH)剂量设定的实验或方法 | 临床前研究和首次人体(FIH)剂量设置的特点 | 监管反馈和临床观察(如适用) |
|---|---|---|---|---|---|---|---|---|---|---|---|
| A1 | 肿瘤 | 免疫刺激剂 | 共刺激分子 (存在形式:可溶性、膜性) | IgG1单抗,靶向在免疫细胞、肿瘤细胞表面表达的新型共刺激激动剂,并作为可溶性系统靶点存在于循环系统中 | 体外实验:细胞因子释放实验 | 同类别首个(FIC) | 高 | 10 mg Q3W (0.125 mg/kg) | 体外"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使用"人体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中的细胞因子诱导数据和最大血清可溶性靶标的10%(即 EC10) | 小鼠替代药以及鼠同源模型作为10% “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的一部分 | 没有监管机构对体外"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衍生的初始剂量表示反对 |
| 根据体外和体内的亲和力差异对分析进行校正 | |||||||||||
| 促进"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介导的对肿瘤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T-regs)的杀伤 | 体内实验:小鼠同基因肿瘤模型以及小鼠替代分子;非人灵长类 | 在临床中,在起始剂量下未观察到"剂量限制性毒性(DLTs)"、输注反应或细胞因子诱导 | |||||||||
| A2 | 肿瘤 | 免疫刺激剂 | CD3 (存在形式:膜性), TAA (存在形式:可溶性、膜性) | 将T细胞和癌细胞上表达的"肿瘤相关抗原(TAA)“进行交叉连接以诱导细胞毒性,以及可溶性"肿瘤相关抗原(TAA)“靶点的存在 | 体外实验:细胞毒性 | 同类别下一个(NIC) | 高 | 计划中的首次人体剂量: 30 μg/kg | 体外"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 (RTCC实验的EC30) | 建议的"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剂量对可溶性"肿瘤相关抗原(TAA)“进行了校正 | 最初建议的30 μg/kg由于RO值过高(90%)而未被监管机构接受。监管机构没有认识到可溶性"肿瘤相关抗原(TAA)“对"首次人体剂量(FIHD)“选择的重要性;因此,监管机构将起始剂量推至3 μg/kg |
| 体内实验: 非人灵长类 | 已确定中的首次人体剂量: 3 μg/kg | 临床观察表明,起始剂量是安全的 | |||||||||
| RO计算 | |||||||||||
| A4 | 肿瘤 | 免疫刺激剂 | 免疫检查点受体 (存在形式:膜性) | 检查点抑制剂 | 体内实验: 非人灵长类 | 同类别下一个(NIC) | 低 | 1 mg/kg 或 80 mg Q2W | 证据权重与既往检查点抑制剂临床"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数据的比较等 | 未提供体外实验数据 | “首次人体(FIH)“剂量被监管机构接受 |
| B1 | 非肿瘤 | 免疫抑制剂 | 免疫细胞靶点 (存在形式:膜性) | 免疫调节剂,人源化IgG1 Ab,具有"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活性,无激动作用,无抑制作用,且无CDC活性 | 体外实验: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 细胞清除(cell depletion)实验 | 同类别首个(FIC) | 高 | 1 μg/kg | 基于"非人灵长类(NHP)“数据的体内"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 | 选择使用基于"非人灵长类(NHP)“数据的体内"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而非体外细胞清除实验(“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用于首次人体剂量设定 | 由于难以将"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活性从体外推断到体内,因此未采用体外"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 |
| 体内实验: 非人灵长类 | 基于体外实验而无需担心"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 | 监管机构同意此策略 | |||||||||
| 在1期试验中未观察到严重的不良反应 | |||||||||||
| H1 | 非肿瘤 | 免疫抑制剂 | CD28 (存在形式:膜性) | 抗CD28拮抗剂结构域抗体与40kDa支链聚乙二醇偶联以延长其系统半衰期 | 体外实验:亲和力测量,受体占有率(RO),混合淋巴细胞反应(MLR) | 同类别首个(FIC) | 高 | 10 μg/70 kg (≒0.14 μg/kg) | 使用体外"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的EC10 | Kd、“混合淋巴细胞反应(MLR)“实验(体外)以及 CD28 的体外-体内关系 | 在体外实验中,未选择体外Kd值作为"首次人体(FIH)“剂量设定,并说明其原因 |
| 体内实验: 小鼠(及小鼠替代物)和非人灵长类中估算的RO和"T细胞依赖抗体反应(TDAR)” | RO (体内) | 临床数据显示,单次剂量为9 mg或更高时,RO≥80%维持≥2周,表明传统的基于毒理学的NOAEL方法是不够的 | |||||||||
| “T细胞依赖抗体反应(TDAR)“用于计算体内"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 | |||||||||||
| H2 | 肿瘤 | 免疫刺激剂 | OX40 (存在形式:膜性) | 共刺激激动剂,完全人源化 IgG1 配体阻断激动性单克隆抗体,高亲和力(Kd 为 50 pM)结合 OX40 | 体外实验:细胞因子释放实验, RO估计 | 同类别下一个(NIC) | 中 | 20 mg | 小鼠同源移植肿瘤模型(基于"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 | 市场上已有的 OX40 激动剂为"首次人体(FIH)“剂量提供了支持 | 小鼠同源移植肿瘤模型被用作"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的一部分 |
| (0.25 mg/kg) | |||||||||||
| 体内实验:小鼠同源移植肿瘤模型; 非人灵长类 | |||||||||||
| H3 | 肿瘤 | 免疫刺激剂 | 免疫检查点受体 (存在形式:膜性) | 检查点抑制剂,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片段晶体可结晶区具有惰性 Fc 功能 | 体外实验:亲和力和RO估计 | 同类别下一个(NIC) | 中 | 1 mg/kg | ≥ 95% 靶点RO的小鼠同源移植肿瘤模型 | 体外效力与竞争对手的比较以及临床经验支持了"首次人体(FIH)“剂量 | “首次人体(FIH)“剂量被监管机构接受 |
| 体内实验: 使用小鼠替代抗体小鼠同源移植肿瘤模型; 非人灵长类 | 体外"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剂量比"首次人体(FIH)“剂量低1000倍 | ||||||||||
| 小鼠同源移植肿瘤模型被用于支持"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 | |||||||||||
| H4 | 肿瘤 | 免疫刺激剂 | 效应细胞共刺激受体(存在形式:膜性), | 效应细胞接合剂,一种含有针对"肿瘤相关抗原(TAA)“和效应细胞共刺激受体结合域的免疫刺激人源化IgG1单克隆抗体 | 体外实验:细胞毒性,效应细胞激活 | 同类别首个(FIC) | 高 | 尚未指明的 (1/8 x 亚毫克) | 体外"药理学活性剂量(PAD)“对应于90%的药理活性 | 与针对相同"肿瘤相关抗原(TAA)“的"T细胞衔接器(TCE)“相比,细胞毒性测定以及在体外诱导最小细胞因子释放的浓度 | 申办方提议将90%的"药理学活性(PA)“作为"首次人体(FIH)",但未被监管机构接受,监管机构认为该产品的平台是一种新颖且未经临床验证的治疗方式。 |
| TAA (存在形式:膜性) | |||||||||||
| 体内实验: 非人灵长类 | |||||||||||
| G1 | 肿瘤 | 免疫刺激剂 | 免疫细胞靶点 (存在形式:膜性) | 免疫刺激型"抗体偶联药物(ADC)",单克隆抗体靶向主要在免疫细胞上表达的蛋白,通过可裂解的连接子与强效的小分子免疫刺激载荷X偶联 | 体外实验:细胞因子释放实验和RO估计 | 同类别首个(FIC) | 高 | 24 μg/kg | 剂量设定在体外"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与"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之间 | 使用体外"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中EC50值 | “首次人体(FIH)“剂量被监管机构接受 |
| 体内实验: 小鼠异种植肿瘤模型; 大鼠毒理学数据; 非人灵长类 | 基于带瘤小鼠体内实验的"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的价值甚至比"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还高 | ||||||||||
| J1 | 非肿瘤 | 免疫刺激剂 | CD3 (存在形式:膜性), unspecified (存在形式:膜性) | 含有"T细胞衔接器(TCE)“和靶向结合臂的双特异性Fc分子 | 体外实验:细胞毒性、T细胞激活和细胞因子释放 | 同类别首个(FIC) | 高 | 0.3 mg | 体外"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EC50) | 目标Cmax为0.1 μg/mL,计算出的"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剂量相当于5 μg/kg | “首次人体(FIH)“剂量被监管机构接受 |
| (5 μg/kg) | |||||||||||
| 体内实验: 非人灵长类 | |||||||||||
| 离体TCR分析 | |||||||||||
| “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建模 | |||||||||||
| K1 | 肿瘤 | 免疫刺激剂 | CD3 (存在形式:膜性), | 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TCE)",采用单抗衍生格式,Fc延长半衰期,含有防止效应功能的突变 | 体外实验:T细胞激活、细胞因子释放测定、细胞毒性活性 | 同类别下一个(NIC) | 高 | 1 ng/kg | 基于细胞毒性的体外"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对应于EC20) | 由于人类的转化不确定性,来自NSG小鼠中人类原发性AML的小鼠肿瘤疗效数据未用于"首次人体(FIH)“剂量确定。 | “首次人体(FIH)“剂量被监管机构接受 |
| CD123 (存在形式:膜性) | 体内实验:小鼠异种植肿瘤模型; 非人灵长类 | ||||||||||
| NJH395 | 肿瘤 | 免疫刺激剂 | TLR7 (存在形式:膜性) | 新型抗癌"免疫刺激剂-抗体偶联物(ISAC, Immune Stimulant Antibody Conjugate)",由小分子TLR7激动剂与抗Her2抗体连接而成 | 体外实验:细胞因子释放实验 | 同类别首个(FIC) | 高 | 0.1 mg/kg Q3W | 基于"非人灵长类(NHP)“细胞因子释放的体内"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 | “多次给药剂量递增研究(MAD)“剂量是基于"非人灵长类(NHP)“的"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确定的,也与"抗药物抗体(ADA)“引起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相关 | “首次人体(FIH)“剂量被监管机构接受 |
| 体内实验: 非人灵长类 | |||||||||||
| L1 | 肿瘤 | 免疫刺激剂 | CD47 (存在形式:膜性), | 一种双特异性抗体,由一个结合CD47的臂和一个结合PD-L1的臂组成,采用人源IgG1格式 | 体外实验:亲和力、共培养实验和RO估算 | 同类别首个(FIC) | 低 | 150 mg SC Q2W | 1/6的"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也用体外"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对应 RO9% 进行了确认 | “首次人体(FIH)“剂量的设定遵循了"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S9 原则,但鉴于潜在的CD47相关靶点相关风险(细胞减少),也在论证中纳入了基于"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的评估。 | “首次人体(FIH)“剂量被监管机构接受 |
| PD-L1 (存在形式:膜性) | |||||||||||
| 体内实验: 非人灵长类 | |||||||||||
| M1 | 非肿瘤 | 免疫抑制剂 | 三种炎症细胞因子(存在形式:可溶性、可溶性、可溶性) | 一种新型多价单克隆抗体构建物,旨在抑制3种可溶性炎症细胞因子的药理活性 | 体外人类药理活性测定 | 同类别首个(FIC) | 中 | 尚未指明的 | “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 | 基于文献资料预测炎症靶组织中3种可溶性靶标的浓度和靶标结合 | “首次人体(FIH)“剂量被监管机构接受 |
| 体内实验: 非人灵长类 |
a 深灰色的产品代表精选的案例。 b 靶点的区分,区分是否以可溶性(S)或膜性(M)形式存在。在 A1 中的“共刺激分子”和 B2 中的“TAA”都同时存在可溶性和膜性形式。 c 安全风险(高、中、低)是基于全部安全信息大致分类的,包括作用机制、目标性质、既往临床经验、非临床安全数据与人体的相关性、非临床不良发现、临床适应症、可监测性等因素。关于首次人体给药起始剂量选择的详细风险因素信息,可以参考 Leach 等人,2021 年。
1)A1:新型共刺激抗体(图 S2)
案例 A1 描述了一种激动型IgG1单克隆抗体(mAb),该抗体作用于一种新型共刺激激动剂——该靶点同时在免疫细胞和肿瘤细胞表面表达,并作为可溶性系统靶点存在于循环系统中。该抗体设计用于激活免疫细胞并促进其浸润至肿瘤微环境,同时促进"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介导的对肿瘤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T-regs)的杀伤。鉴于以下特征:靶点表达的广泛性、直接的免疫激活活性、在免疫细胞膜上的表达特性,以及在常规毒理学试验动物中靶点缺失或低表达的现象,A1的理论风险被判定为较高,因此"首次人体试验(FIH)“采用了基于"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的起始剂量。
A1仅与高亲和力(类似于人类抗原)的食蟹猴发生交叉反应;因此,我们在食蟹猴中进行了为期4周的GLP毒理学研究,在10和100 mg/kg的剂量下,没有观察到不良反应。随后,”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设定为100 mg/kg。然而,由于靶基因在正常猴子中的表达非常低,因此我们制备了一种小鼠替代mAb(嵌合mAb),并用于"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和小鼠同系肿瘤模型的疗效研究,这些研究是确定”首次人体(FIH)”剂量的关键。替代mAb的毒代动力学(TK)表现出非线性的药代动力学,这可能归因于靶介导的药物处理(TMDD),表明A1可能与小鼠免疫细胞上表达的膜靶结合,同时降低可溶性靶浓度。
由于食蟹猴毒理学研究将导致过高的起始剂量(“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 =16.7或”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 10 mg/kg),”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主要是根据小鼠的替代"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数据确定的。为了估算”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分析包括利用同系肿瘤模型的替代mAb数据建立"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模型,根据小鼠数据计算”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剂量(即靶点抑制),并针对小鼠靶点的替代mAb和人类靶点的A1之间的结合亲和力差异进行调整,以及将"药物代谢动力学(PK)“参数从小鼠和猴子缩放到人类。”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被设定为在预计的平均稳态Cmax引起血清可溶性靶点10%抑制的剂量,从而获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Health Authority)“批准的10 mg Q3W的”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临床上,这一剂量未显示出剂量限制性毒性、输液反应或细胞因子诱导。
该案例强调了免疫激活疗法的潜在路径,这些疗法在人类中有毒性风险,但在健康猴子中无毒性,主要原因是靶点表达低/无。使用替代单克隆抗体和具有更多人类相关靶点表达的小鼠肿瘤模型进行"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评估可能更适合预测”首次人体(FIH)”剂量。回顾性分析发现,基于"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模型的”药理学活性剂量(PAD)”(即300 mg)在临床中被设定为起始剂量是更为合适的。该剂量在未引起"DLT(剂量限制毒性, dose-limiting toxicities)“的前提下展现出更强的药理学效应,尤其考虑到最终推荐剂量设定为”药理学活性剂量(PAD)”的约5倍水平。
2) H4:效应细胞"衔接器(engager)“单克隆抗体(图S3)
H4是在野生型IgG1框架上含有针对"肿瘤相关抗原(TAA, tumor-associated antigen)“和效应细胞共刺激受体的结合域的免疫刺激性人源化双特异性mAb。目前正在开发H4用于治疗严重和危及生命的癌症。考虑药理学和毒理学研究数据,选择H4的”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对于基于药理学数据的”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估算,使用H4介导的靶细胞杀伤和效应细胞活化来计算产生约90%最大"药理学活性(PA, pharmacologic activity)“的浓度。90%的”药理学活性(PA)”会产生亚毫克的”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计算基于90%”药理学活性(PA)”的起始剂量,而不是使用”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 30%”药理学活性(PA)”)的基本原理是,与针对相同"肿瘤相关抗原(TAA)“的另一种免疫刺激双特异性mAb (“T细胞衔接器(TCE, T cell engager)")相比,使用H4时观察到显著较少的细胞因子释放。在药理学研究中,与"T细胞衔接器(TCE)“相比,H4对相同"肿瘤相关抗原(TAA)“在相似浓度下的细胞因子释放显著较少,这导致了一个可检验的假设,即基于上述90%”药理学活性(PA)”计算的起始剂量的H4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风险较低且可管理。
基于毒理学的H4”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是基于在食蟹猴中进行的1个月重复剂量毒性研究的”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确定的,食蟹猴是唯一的药理学相关物种,基于TAA和共刺激受体的表达以及与人类相比的表位结合亲和力。在猴子中未观察到细胞因子释放。根据已接受的监管指南(ICH S9),应用6倍的安全系数,从”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计算出的”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约为根据药理学数据(90%”药理学活性(PA)”)获得的剂量的1,000倍。尽管”首次人体(FIH)”的估计起始剂量较高,但由于H4是一种免疫刺激分子,在人体中可能具有不可预测的毒性,因此我们需要采用相对保守的方法,并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Health Authority)“提出了基于90%”药理学活性(PA)”的亚毫克起始剂量(即”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图5)。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Health Authority)“不接受此”首次人体(FIH)”的起始剂量,强调这是一种未经临床测试的新方法,并指出不适合将细胞因子释放数据与其他分子的数据进行比较。根据“卫生/健康行政部门(Health Authority)“的建议,”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降低约8倍,且”药理学活性(PA)”约为40-50%(即”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因此临床研究中增加了两个队列。
3)新型免疫刺激性抗体偶联物(图 S4)
NJH395是一种新型的抗肿瘤"免疫刺激性抗体偶联物(ISAC, Immune Stimulant Antibody Conjugate)",由一个小分子TLR7激动剂偶联到一个临床验证的抗体。
我们在食蟹猴中进行了多项研究,以评估NJH395的"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关系。在食蟹猴中,NJH395以3 - 30mg /kg的剂量单次静脉给药,0.1 - 10mg /kg的剂量每3周一次进行多次静脉给药。根据毒代动力学数据,NJH395表现出非线性"药物代谢动力学(PK)",这是由于快速治疗产生的抗NJH395抗体,影响了后续剂量的暴露。“抗药物抗体(ADA, anit-drug antibodies)“应答的很大一部分针对TLR7激动剂小分子,一些靶向mAb的可变区。此外,“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分析确定,治疗诱导的"抗药物抗体(ADA)“没有阻断或增加细胞因子的释放。TLR7激动剂的代谢物在猴血清中非常显著,在第2剂的3和10mg/kg的NJH395后,其主要活性代谢物的蓄积超过45倍。
药物效应动力学终点分析显示,NJH395的0.1和0.3 mg/kg剂量未导致超过基线波动范围的细胞因子升高,也未出现炎症的临床症状。NJH935单次给药3 mg/kg和10 mg/kg 可导致血清IL-6升高和心率加快。1mg/kg重复给药后6到12小时内,细胞因子(如IL-6, IP-10, IL-1RA, MCP-1和I-TAC)的升高更为明显。这导致第三次后心率加快;然而,心电图确定了QT延长的风险极低。30mg /kg剂量导致血清细胞因子升高,组织中明显的炎症,尤其是在大脑中,导致病变的发生。根据这些数据,体内细胞因子释放的”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被确定为0.3 mg/kg。
在一项为期7周的GLP “非人灵长类(NHP)“研究中,NJH395以3或10 mg/kg的剂量单次给药,或以1 mg/kg的剂量每3周给药1次共给药3次。与"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研究一致,NJH395 显示血清细胞因子增加,且因抗药物抗体(“抗药物抗体(ADA)“在给药后 96 小时存在而时间依赖性地清除率提升,影响后续剂量后的暴露,并似乎增强细胞因子的释放。在1和3 mg/kg后出现的急性期反应(即炎症)在3周恢复期内得到消退。组织病理学结果与T细胞激动和相关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相关。尽管未进行后续研究,但推测TLR7激动剂及其活性代谢物的暴露由于相关"抗药物抗体(ADA)“增加,导致随后给药后细胞因子释放增加。基于这些观察结果,多次给药的"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被确定为1 mg/kg。
“首次人体(FIH)“研究分为两部分:(i)“单次给药递增剂量(SAD, Single Ascending Dose)“和(ii)“多次给药递增剂量(MAD, Multiple Ascending Dose)"。考虑到新颖的作用机制,I期研究设计为在进入"多次给药剂量递增研究(MAD)“阶段前先进行"单次给药剂量递增研究(SAD)"。该方法旨在获得患者的初步安全性,以降低在多次给药环境中后续剂量的风险(如”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抗药物抗体(ADA)”)。
在"单次给药剂量递增研究(SAD)“研究中,“首次人体(FIH)“的起始剂量是使用基于"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的方法估算的,并整合了来自食蟹猴药"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研究的数据,因为这比细胞因子释放数据更相关,在0.3 mg/kg的剂量下,未观察到IL-6(安全性相关的细胞因子)或IP-10 (“药物效应动力学(PD)“相关的细胞因子)超过基线水平的增加。随后,基于FDA指南建议,将0.3 mg/kg剂量换算为"人体等效剂量(HED)“后为0.1 mg/kg。与食蟹猴单次给药的可耐受剂量10mg/kg相比,预测的"单次给药剂量递增研究(SAD)“研究在AUC和Cmax方面的"安全裕度(safety margins)“分别为343倍和93倍。“多次给药剂量递增研究(MAD)“研究的起始剂量是基于食蟹猴GLP毒理学研究中的多次给药的”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估算,因为重复给药后,由于"抗药物抗体(ADA)“的增强作用,对"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的顾虑更高。猴子”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确定为1 mg/kg,由此推算患者的"最大推荐起始剂量(MRSD)“约为0.05 mg/kg。与经过临床验证的单克隆抗体一样,“多次给药剂量递增研究(MAD)“将遵循每三周一次(Q3W)的给药方案。“卫生/健康行政部门(Health Authority)“接受了这一做法。
在临床中,NJH395的"单次给药剂量递增研究(SAD)“使用的起始剂量为0.1 mg/kg每3周1次,剂量递增2倍。正如预期的那样,在患者中观察到的主要不良事件是"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55.6%),发生于所有剂量水平。3名患者在0.2 mg/kg(n = 1)和1.6 mg/kg(n = 2)剂量下出现了"剂量限制性毒性(DLTs)",原因包括3级AST升高、脑膜炎或脑膜刺激症状。NJH395表现出非线性药代动力学。此外,给药后96小时,100%的患者对NJH395出现了"抗药物抗体(ADA)",与临床前研究结果一致。随后的分析确定,44.4%的患者对NJH395产生了中和抗体。由于担心多次给药后可能因"抗药物抗体(ADA)“水平升高而增强"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以及有限的临床获益,因此未评估"多次给药剂量递增研究(MAD)“阶段。此案例表明,对于某些分子,例如"作用机制(MoA)“可能导致免疫原性风险增加的分子,非临床免疫原性数据确实反映了随后的临床免疫原性数据。
4) J1:用于非肿瘤适应证的T细胞衔接器(图S5)
J1是一种基于IgG1的双特异性分子,可同时结合T细胞和靶细胞上表达的CD3,用于治疗非肿瘤性适应证。尽管靶点在全身循环系统和组织中都有表达,但据估计患者群体中的靶点表达非常低,理论上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潜在风险。
鉴于适应证是非肿瘤学,在非临床评估和选择"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时,关键考虑因素是充分降低患者主要安全问题的风险,例如非特异性和靶向T细胞激活和细胞因子释放。食蟹猴被确定为部分相关物种(仅与食蟹猴CD3有交叉反应),以确定与J1的CD3臂接合相关的任何非特异性活性。可以在猴子体内充分评估CD3+T细胞的浓度依赖性和非特异性激活以及其引发的细胞因子释放的风险。J1通过静脉输注给药,剂量为每周1次(QW)10、30和100 mg/kg,共给药五次。每周1次的给药方案选择是基于猴子约6天的半衰期。根据ICH S6(R1),高剂量的选择是基于临床预期最大暴露量的≥10倍暴露量的倍数。简而言之,在测试的最高剂量下,未观察到供试品相关的不良反应或不良细胞因子诱导。J1 “毒代动力学(TK)“在评估的剂量范围内与剂量成正比。“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被设定为测试的最高剂量,并且考虑到猴体内缺乏靶点,相关"安全裕度(safety margins)“不被认为是对"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的确定的决定性因素,但总体数据表明T细胞的非特异性激活风险最小。
J1的"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采用改良的"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计算的,该方法建议使用最相关的测量值,而不是最敏感的药理学活性测量值。用于决策的数据包包括:(i)原代细胞杀伤实验中的靶细胞杀伤和细胞因子释放,(ii)健康供体和患者中的T细胞活化和细胞因子释放,以及(iii)共培养实验中靶点细胞杀伤的靶向与非靶向窗口。在原代细胞杀伤实验中,细胞杀伤中位数EC50为0.12 μg/mL。此外,在患者来源的"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s)“中,在0.1 μg/mL浓度下未观察到可测量的T细胞活化或细胞因子释放,在健康供体血浆中,也未检测到在0.1 μg/mL浓度下的可测量细胞因子水平(10-plex panel)。最后,在共孵育实验中,T细胞活化的靶向与非靶向EC10存在超过100倍的差异。尽管Saber等人2017建议以10–30%的药理活性作为FIH剂量是一种可接受的方法,但从原代细胞杀伤实验中获得的中位EC50被认为是J1活性的最相关指标,并且该指标与任何细胞因子释放无关。因此,“首次人体(FIH)“的起始剂量(即最大血浆浓度或Cmax 达到0.1 μg/mL所需的剂量)估计为0.3 mg (5 μg/kg)。
尽管使用RO方法进行首次人体剂量选择(FIH)不可接受,但三聚体RO被认为是支持信息。简而言之,一个包含靶点组织房室的"最小的基于生理的药代动力学(mPBPK)“模型被用于拟合J1的预测人体血清和组织"药物代谢动力学(PK)“数据。该模型还包括CD3 T细胞和靶点细胞水平、每个细胞的CD3和靶点拷贝数、CD3臂的亲和力以及靶点臂的亲和力范围(以考虑临床上靶点亲和力的变异性)。模型预测显示,在"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0.3 mg Q2W静脉注射后,稳态平均浓度下,三聚体RO在血清和靶组织中的比例将低于1%。这些模拟进一步支持了体外实验中J1在0.1 μg/mL浓度下未观察到有意义的T细胞激活或细胞因子释放的结果。
总之,与J1最相关的"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是从原代细胞杀伤试验中获得的EC50(0.1 μg/mL),FDA批准了拟定的"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0.3 mg。
5) B1:用于过敏性疾病的单克隆抗体(图S6)
B1是一种人源化IgG1单抗,其"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活性通过修饰增强,用于过敏性疾病的特异性适应证。“首次人体(FIH)“剂量计算采用"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和"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建模方法,结合B1的作用机制、靶分子(靶点)性质和非临床研究结果。由于B1只与猴和人靶点结合(具有相似的亲和力),因此猴被选为最具药理学相关性的非临床物种。
在对食蟹猴进行的8周重复剂量毒性研究中,“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被认为是100mg /kg。根据"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方法和10倍安全系数,人体初始剂量被计算为10 mg/kg。体内"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是根据"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猴子研究中"靶点表达(target-expressing )“细胞数量的减少估算的。根据血液中表达靶细胞的不同,“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被认为是0.001 ~ 0.01 mg/kg。还用人类血液进行了体外"细胞清除(cell depletion)“实验。B1在0.1到1 ng/mL时可清除"靶点表达(target-expressing )“细胞,但考虑到从体外到体内"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活性难以外推,未将结果用于"首次人体(FIH)“剂量设定。
为了进一步支持"首次人体(FIH)“的研究,体外评估了B1对人外周血细胞因子释放的影响。在少数供体中,B1可诱导少量的IL-6和IFN- γ细胞因子释放,但细胞因子浓度接近定量下限且无浓度依赖性。此外,在猴子毒理学研究中,B1 输注超过15分钟后未见明显细胞因子升高。基于"作用机制(MOA)“及上述结果,我们不认为"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对"首次人体(FIH)“剂量构成风险。
基于食蟹猴研究的数据进行了"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建模和模拟,以支持基于"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的剂量,估算出的人类"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剂量为0.001 mg/kg。综合考虑,一方面"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计算的"首次人体(FIH)“剂量为10 mg/kg,另一方面,“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表明"首次人体(FIH)“剂量为0.001 mg/kg,鉴于B1是一种具有免疫刺激功能的强效免疫细胞清除剂,最终依据体内"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研究结果,将B1的初始剂量设定为0.001 mg/kg。监管机构同意了该建议的策略。在1期"健康志愿者(HV, healthy volunteer)“研究中,B1在所有测试剂量下,包括0.001 mg/kg的"首次人体(FIH)“剂量,均观察到比预期持续更长时间的"靶点表达(target-expressing )“细胞的清除作用。1期试验中未观察到严重不良反应。综上,体内"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剂量在患者中显示了药理活性,该剂量的设定科学合理且并非过于保守,但其作用持续时间超出了预期。基于这些观察结果,可能需要进一步优化"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模型,在其中考虑其它"药物效应动力学(PD)“参数,例如,靶细胞周转的种属差异,这可能为剂量方案设计提供更多见解。
6) H3:检查点抑制剂单克隆抗体(图S7)
H3 是一种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其具有功能惰性的Fc区。它的作用靶点是免疫检查点受体,用于肿瘤相关适应症。H3 的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是根据毒理学和药理学研究数据选定的。此外,还参考了针对同一靶点的"竞品抗体-A(CMP-A, competitor antibody A)“的临床安全经验,通过制造"竞品抗体-A(CMP-A)“的内部版本并与 H3 进行并排比较(即"反向转化(reverse translation)"),来指导起始剂量的选择。
基于毒理学的起始剂量是基于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 100 mg/kg/week),或相当于"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该剂量是根据食蟹猴(唯一药理学相关物种)中进行的1个月重复剂量毒理研究确定。应用6倍的安全系数,人体起始剂量计算为16.7 mg/kg。在药理学方面,利用小鼠替代单克隆抗体的抗肿瘤有效性数据预测人体有效剂量。具体的来说,评估了小鼠同系肿瘤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中的靶点受体占有率(RO)并与抗肿瘤疗效相关联。研究发现,当肿瘤中靶点谷浓度靶点RO≥95%时,在小鼠中实现了稳健的抗肿瘤疗效。要使人体肿瘤达到同等RO水平,预测H3的人体有效剂量为2.5 mg/kg。由于预测的有效剂量为2.5 mg/kg,故将起始剂量设定为1 mg/kg,降低1个剂量水平,以确保足够的安全性。此外,同时也使用了一种"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进行了剂量预测,该MABEL方法假设峰浓度时血中RO达到50%,其中的RO源自体外RO实验,1 mg/kg的起始剂量比采用这种MABEL方法预测的剂量高出3000倍以上。
起始剂量的选择从"竞品抗体-A(CMP-A)“的临床安全经验得到了支持。“竞品抗体-A(CMP-A)“的"2期推荐剂量(RP2D, recommended Phase 2 dose)“为每2周静脉注射10毫克/公斤(10 mg/kg i.v. Q2W)。在这一剂量下,药物的耐受性良好,未达到"最大耐受剂量(MTD)"。此外,文献中未报道该分子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输注相关反应(IRR, infusion related reaction)"。当将体外的KD与人血RO EC50并排比较时,H3在临床中的"效力(potent)“比"竞品抗体-A(CMP-A)“高1.3 ~ 2.7倍。将剂量按体外效力的差异(3倍及以上)标准化后,H3的起始剂量1 mg/kg比竞品临床中"2期推荐剂量(RP2D)“的10 mg/kg低3倍。此外,H3在体外和在食蟹猴中未发现细胞因子释放风险。结合临床中观察到的同一靶点未观察到"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输注相关反应(IRR)",H3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风险被认为较低。
总之,H3的所有临床前药理学和毒理学数据支持1 mg/kg的起始剂量。基于同一靶点的临床安全经验以及与临床分子"竞品抗体-A(CMP-A)“的体外效力并排对比,进一步证明了起始剂量的合理性。随后,该起始剂量在"首次人体(FIH)“试验中成功实施。
7) M1:用于非肿瘤适应证的细胞因子阻断三特异性单抗(图S8)
M1是一种基于单抗的新型多价构建物,旨在抑制三种可溶性炎症细胞因子的药理活性。它正在临床开发中,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这三个靶点的表达和功能已经被明确,并且针对单个细胞因子的单抗有相当多的临床经验,包括已批准的单抗。预计不存在急性毒性风险。对人体的主要风险长期给药后可能增加感染风险,这是由于固有免疫受到其抑制(许多此类靶向细胞因子的免疫抑制性单克隆抗体都会出现此情况)。M1对三种食蟹猴同源细胞因子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和中和作用,中和作用程度与人细胞因子相似。M1不抑制来自啮齿动物或其他低等物种的三种细胞因子。M1在"非人灵长类(NHPs)“中具有良好的耐受性,但由于一些动物因皮肤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其他细菌增殖而出现不良皮肤脓肿和皮炎,因此无法确定"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食蟹猴的这类感染相关事件之前已被证明不会直接转化到人体。通过体外人源样品药理学活性实验可用于在临床相关的生物活性实验中确定该构建物对三种人类细胞因子中每一种的效力。因此,基于拮抗剂的作用机制、对靶点的现有知识、可获得的药理相关体外和体内模型以及单药治疗的临床安全性经验,我们认为"首次人体(FIH)“研究参与者发生不良安全性事件的风险不高。因此,没有提出基于标准"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的起始剂量。
出于安全性考虑,在确定"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时,考虑了血液和靶组织中对三种细胞因子的结合情况。使用了M1的人体"药物代谢动力学(PK)“参数估计值,以及"毒代动力学(TK)“数据和预测的药理学效应。由于"首次人体(FIH)“研究是在轻度炎症性疾病患者中进行的,因此需避免非常低的RO,以尽量减少接受亚治疗暴露的患者数量。起始剂量定义为在靶组织中获得一定水平的靶点结合的剂量。血液中对单个细胞因子结合预计不会产生显著的药理学效应(基于大量的外部和内部数据);因此,血液中更高水平的靶点结合是可以接受的。
在不同的体外实验中,生成了M1对三个靶点的多种结合亲和力的值。在体外细胞实验中选取了在能够在细胞上诱导三种细胞因子各自50%最大反应下的浓度作为获得的EC50值,因为它更能代表体内情况,用作计算M1对这些细胞因子结合百分比的效力值。针对可溶性内源性细胞因子的单克隆抗体的多靶点周转模型用于预测血浆和靶组织中3种细胞因子的结合百分比。血液中细胞因子的表达数据来自"内部(in-house)“数据和文献。炎症靶组织中的表达则衍生自文献数据。单克隆抗体在组织中的分布范围为10% ~ 50%,在模拟中假设为30%。选定的起始剂量下预测的三种细胞因子在靶组织中的靶的结合程度分别达到20%、10%和95%。虽然,其中两种细胞因子预测的靶点结合程度较低,并且发挥的药理学效应极小,但第三种细胞因子的结合可能在起始剂量时产生药理学效应。鉴于在中和该细胞因子方面已拥有广泛的非临床和临床经验,因此发生重要不良事件的风险被认为较低。选定的起始剂量下,血液中所有三种细胞因子的靶点结合率预计大于95%。在起始剂下预测的暴露量Cmax和AUC都比在猴子中最低给药剂量后观察到的最高暴露量低数百倍(因为在毒理学研究中没有建立"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综上所述,由于毒理学研究中未发现"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因此M1利用"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模型来选择首次人体剂量。
讨论
对免疫抑制剂和免疫刺激剂进行的"首次人体(FIH)“剂量风险评估有很大差异,包括获益和潜在危害的复杂相互作用,并根据患者的需求和特定医疗条件量身定制。免疫抑制剂的风险通常低于免疫刺激剂,因为感染等不良事件通常不是急性的,严重程度较低,不会危及生命。此外,通常观察到的与免疫抑制剂作用机制相关的不良事件需要长期暴露和积累,而免疫刺激剂的不良事件主要由Cmax驱动,通常是短暂的(适当的治疗干预),但立即发生的。因此,免疫抑制剂的"首次人体(FIH)“剂量策略通常遵循毒理学方法,如"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或"药理学活性剂量(PAD)"。相反,“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可能适用于有过度刺激特异性免疫应答风险的免疫刺激剂,这些风险会导致更严重和危及生命的情况,如TGN1412观察到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虽然"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用于免疫刺激剂的"首次人体(FIH)“剂量已经防止了类似TGN1412的事件,但它也导致了不必要的负担,特别是在涉及亚治疗剂量的癌症治疗中。Leach等人提出了“非"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以数据驱动和/或基于风险的方式避免所有生物药的过低的"首次人体(FIH)“剂量,并提供一个基于风险评估的决策树来指导是否应该考虑"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在本文中,我们结合11家成员公司的调查回复和详细的案例研究,针对生物免疫调节剂的"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进行了专门讨论。此外,我们在"药物开发创新和质量国际联盟(IQ Consortium,)“提出的决策树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修订后的决策树来帮助指导"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
本文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提供详细的案例,描述生物免疫调节剂的FIH起始剂量论证过程,然后应用这些案例研用于演示与说明修订后的决策树该如何使用(图4)。当将所有8个案例的决策过程(见图S2-S9)在一起进行分析时(图5),可以明显看出这些研究中FIH剂量设置的调整得到了有效管理。这是基于ECx或RO%值,并且与风险/获益顺序一致,特别区分了免疫刺激剂和免疫抑制剂,以及区分了"同类别首个(first-in-class)“和"同类别下一个(next-in-class)"。这一发现与受访公司的调查结果一致(图2和3,表S1)。
/image-20260203221244379.png)
图5 八个案例中沿着决策树的FIH剂量设置调整情况。
对八个案例按其推定的"首次人体(FIH)“剂量从低到高排列。在单个产品中从三个剂量设定的选项(“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药理学活性剂量(PAD)“和 “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中选择 “首次人体(FIH)“剂量所使用的方案,以及随后沿各个决策选项的微调,似乎都取决于两个主要风险因素的组合,即“类别(免疫刺激剂或免疫抑制剂)”和“作用机制的新颖性(FIC 或 NIC)”。例如,“红色”标记(免疫刺激剂和 FIC)的组合,表示该产品风险较高,更可能采用 “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确定 “首次人体(FIH)“剂量(A1、H4、NJH395 或 J1)。相比之下,如果上述组合中的任一因素被标为“蓝色”(免疫抑制剂和 NIC),表示风险较低,则该产品更可能采用 “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或 “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方法(B1、H3、M1 或 A4)。当将来自不同公司的八个案例研究整体概览时,基于这些数值对 “首次人体(FIH)“剂量的调整很可能是按照这些免疫调节剂的风险/获益顺序进行的(粗黑箭头),这也验证了受访公司调查结果(图 2 和 3,表 S1)。关于每个单独案例的 “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图 S2–S9。FIC 表示"同类别首个(first-in-class)",NIC 表示"同类别下一个(next-in-class)"。*A4 未包含在正文中,仅包含在表 1 中。
这些详细的案例中有许多是免疫刺激剂的例子,通常认为免疫刺激剂的风险高于免疫抑制剂。三个案例(#1、2、3,“同类别首个(first-in-class)")被确定为风险较高的案例研究,原因是靶点广泛表达(案例#1),直接的免疫激活活性(案例#1、2、3),毒理学物种中缺乏靶点表达(案例#1),以及潜在的临床相关"抗药物抗体(ADA)“增加药物暴露和"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案例#3)。由于潜在的作用机制,案例#3采用"单次给药剂量递增研究(SAD)“与"多次给药剂量递增研究(MAD)“联合试验设计,因其临床前研究显示免疫原性风险较高。值得注意的是,在考虑TLR 7激动剂时,尽管"人体等效剂量(HED)“换算和体表面积的安全系数通常不适用于生物制品,但还是进行了使用。对于案例1和案例3,“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剂量均得到了监管机构的充分认可。另一方面,案例#2最初根据Saber等人2017年的指南建议了"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剂量,但认为过于保守(即30% “药理学活性(PA)"),并尝试设定更高的起始剂量,相当于90% “药理学活性(PA)"(即"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监管机构不同意基于90% “药理学活性(PA)“的"首次人体(FIH)“剂量,并建议申办方将剂量降低到40–50% “药理学活性(PA)"。基于上述三个案例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高风险的新型免疫刺激剂,监管机构更倾向于采用"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而不是"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新型免疫刺激剂可能带来的未知毒性风险较大,监管机构可能建议使用"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以降低患者风险。然而,由于"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常常导致首次人体试验使用的亚治疗剂量,因此需要额外的患者队列,这在案例#2中显而易见。
其余四个案例研究被认为是低到中等风险,因为每种分子都未表现出高风险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毒理学研究中的安全性问题,和/或现有的临床数据降低了该类别分子的风险。案例#6的剂量论证是最简单易懂,这是一种针对肿瘤的新型检查点抑制剂,风险较低。鉴于基于"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的"首次人体(FIH)“剂量对于低风险新型检查点抑制剂而言似乎过高,申办方选择了基于"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50% “药理学活性(PA)")估计的约17倍低的"首次人体(FIH)“剂量,并使用了任意安全系数。然而,在临床研究中,不使用任意安全性因子会排除一个队列。
对于另外两个非肿瘤适应症案例,“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驱动了起始剂量的选择。在案例#5中,重点介绍了一种用于过敏性疾病的Fc修饰的单抗,其中驱动药理活性的"作用机制(MOA)“为"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该申办方选择了"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因为该分子被视为具有免疫激活活性的强效免疫细胞清除剂,起始剂量为0.001 mg/kg。监管机构同意申办方的评估,临床中该剂量耐受性良好。值得注意的是,利用猴子数据进行"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建模低估了基于临床数据免疫细胞清除作用的持续时间,并进一步说明可能需要进一步参数优化,以更准确地预测该类分子在非肿瘤适应症中的表现。案例#4很有趣,该分子是非肿瘤适应症的CD3 T细胞衔接器,但选择了Saber 2017等人建议的"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剂量,尽管该分子因患者靶向表达极低被认定为低风险。独特的是,没有针对靶细胞抗原的药理学相关物种,但申办方表示猴子因与CD3的交叉反应性,仍是相关物种;因此,预期临床前研究中不会有严重不良事件,这一点通过其"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设定为100 mg/kg得到证实。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监管机构可能不同意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际上是相关药理物种,因此可能会要求使用疾病(即异种移植)小鼠模型或使用替代分子来表征靶点相关毒性。这与国际3R原则“减少、优化、替代”相符。反思这一策略,可以提出不进行猴子研究的理由,因为"T细胞衔接器(TCE)“在缺乏靶细胞抗原的情况下不应诱导T细胞活性,而靶细胞抗原可以在体外评估。尽管如此,本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当缺乏药理相关物种时,可以使用"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案例#4的一个重要且独特的方面是使用"基于生理的药物代谢动力学(PBPK)“建模来证明"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剂量的合理性。PBPK可以提供自下而上的剂量选择方法,因为这些模型可以整合药物特性和生理参数(如组织靶点表达、血液和淋巴流量等),从而推导重要的"药物代谢动力学(PK)“终点,如RO或三聚体数,从而将预测的患者组织浓度与体外实验(尤其是非肿瘤适应症)联系起来。最后,案例研究#7是一种针对非肿瘤适应症的免疫抑制三特异性抗体,重点是阻断细胞因子和减轻免疫反应。风险被认为极低,因为没有急性毒性,患者关注的主要风险是由于固有免疫长期受抑制导致感染增加。与本文描述的其他低风险分子不同,案例研究#7确定使用标准MABEL的起始剂量不合理,因为该分子在猴子中耐受性良好,风险较低,并且针对三种细胞因子的单一治疗的临床安全性经验降低了"作用机制(MOA)“相关安全性的风险。这促使申办方采用"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模型来选择剂量(即,所有三种细胞因子的RO> 95%)。
对于低风险分子来说,确定真正的"未见明显毒性反应剂量(NOAEL)“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些分子在其药理相关物种中高剂量下通常耐受良好,这导致研发方倾向于采用替代方法,主要是基于"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和"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的策略。尽管"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通常用于高风险分子,但具有新颖"作用机制(MOA)“或难以转化到临床的低风险分子,也可能使用"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特别是在健康志愿者或非肿瘤适应症中。然而,如果申办方在肿瘤适应症中使用"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应仔细评估所选剂量是否会提供"亚治疗(sub-therapeutic)“活性。因此,申办方可能希望考虑"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建模,同时利用相关的体外和体内数据来证明肿瘤中安全但潜在的治疗剂量(图S10)。
我们的调查和相关案例表明,对于免疫刺激剂(尤其是结合"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模型时),体外实验所能提供的见解可能比既往认知更为深入。例如在CD3双特异性抗体研发中,细胞因子释放实验曾因无法充分证明剂量合理性被FDA明确否决。体外细胞因子释放评估是免疫刺激性单克隆抗体及其它直接或间接激活免疫细胞的治疗性蛋白(如T细胞衔接器)非临床安全性评估的一部分,如案例研究1–7所示。这类体外实验通常在人全血或外周血单核细胞中以可溶或固定化的形式进行。在可溶"细胞因子释放(CR)“实验格式中,药物浓度易于获得,且"细胞因子释放(CR)“的无效水平可能可用于换算剂量,作为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选择的参考,如果该方法符合"作用机制(MOA)“的要求。如果药物被固定在表面上,则无法可靠地对应药物浓度。在这种情况下,药物浓度可以通过将涂于板上的药物量除以孵育体积来近似。当将"细胞因子释放(CR)“与TGN1412、利妥昔单抗和Campath-1H相关联时,这种方法似乎是足够的。然而,该领域可能需要进一步探索这种或其他方法,以更好地理解体外"细胞因子释放(CR)“结果,为"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选择提供指导。此外,如果理解了种属差异和"细胞因子释放(CR)“作用机制,或者体外与非临床物种体内"细胞因子释放(CR)“存在相关性,那么非临床物种的体内"细胞因子释放(CR)“数据也可以指导"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选择,从而利用人体体外数据。一个良好的例子是CD20 T细胞衔接器glofitamab的"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在该例中,“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建模被用于定量整合猴体内"细胞因子释放(CR)“数据以及猴和人类的体外"细胞因子释放(CR)“数据,并将结果转化为人类的起始剂量,同时考虑健康猴与癌症患者之间"细胞因子释放(CR)“的潜在差异。
肿瘤学最近的快速发展将免疫调节剂推上了前沿,因此申办方迫切需要探索更长的治疗持续时间、更丰富的给药方案和以及超越"最大耐受剂量(MTD)“策略的替代方法。认识到这一差距,FDA启动了"擎天柱项目(Project Optimus)",以改革和加强关键性/注册性试验中对申办方剂量选择的指导。虽然最初的指南提供了一个框架,但仍存在问题,特别是在联合治疗和"同类别首个(first-in-class)“分子靶点方面。虽然"擎天柱项目(Project Optimus)“主要关注临床试验启动后的剂量优化,但其许多原则也可延伸至选择"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以便在后期开发阶段实现更高效的剂量优化。例如,我们的文章描述了不同申办方在模式类型、靶点、给药方案和/或监管意见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方法选择免疫调节剂剂量的经验。随着"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模型在将临床前数据转化为"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多,这些模型可以通过输入的临床数据进行验证,并在剂量优化过程中加以利用。总之,该策略有望提高效率,加快患者获得新型、可能更有效抗癌药物的机会。
关于"首次人体(FIH)“剂量,“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免疫安全技术委员会(ITC)“强调了几个关键点。首先,它指出"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往往被过度使用,这与"药物开发创新和质量国际联盟(IQ)“的观点一致。“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免疫安全技术委员会(ITC)“主张应用 “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以平衡药理活性与安全性。此外,“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免疫安全技术委员会(ITC)“建议在适当情况下使用"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建模,以提高给药策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然而,“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免疫安全技术委员会(ITC)“也承认"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仍具有价值,特别是在用新型免疫调节剂进行健康志愿者研究时,因为它可以降低风险,从而让患者能够使用更高、更具药理活性的剂量。
结论
这里展示的研究结果突出了业内对免疫调节"首次人体(FIH)“起始剂量选择策略的看法,这些策略通过一系列针对性且详尽的案例研究加以说明。这些观察促使对Leach等人2021年提出的指南进行了优化,包括一个更全面的流程图,以便未来为受试者提供更加简化的"首次人体(FIH)“剂量选择。此外,我们的行业调查显示,由于免疫调节生物制剂的风险收益比高于非免疫调节生物制剂,“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已成为最常用的策略。然而,申办方指出,“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方法往往被过度使用,因此明确提出了对"药理学活性剂量(PAD)“方法和"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建模的建议和支持。基于这些观察,“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免疫安全技术委员会(ITC)“工作组建议在适用情况下“超越‘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使用替代策略(例如"药理学活性剂量(PAD)"、“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或整体/整合方法)为患者提供起始剂量,以增加在治疗范围内的可能性,或者能够在不损害安全性的情况下快速达到最佳剂量的治疗剂量。
致谢
作者衷心感谢"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免疫安全技术委员会(ITC)“和首次人体剂量项目组的政府、学术和工业界科学家对这项工作的贡献,以及"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科学项目经理Stanley Parish、E’lissa Flores、Lucilia Mouries、Shermaine Mitchell-Ryan和Chrissy Crute的支持。作者还感谢Michelle Coulson(诺华)、Carole Harbison(武田)、Jonathan Heyen(辉瑞)、Karen Price(强生)、Pavan Vajjah(阿斯利康)和Delphine Valente(赛诺菲)对文稿案例的贡献。
资金
该"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科学计划主要由公共和私人部门参与者提供的实物贡献(包括时间、专业知识以及实验和/或开发工作)支持。这些贡献通过"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企业赞助商提供的直接资金得到补充,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项目基础设施和管理以及部分项目相关的直接费用。支持组织(公共和私人)的列表可在 http://hesiglobal.org 查阅。“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是一个非营利科学组织,促进公共与私人在人体健康与环境健康方面的合作。“免疫安全技术委员会(ITC)“致力于识别和解决与免疫安全相关的科学问题,并将其转化为人体健康风险评估。
利益冲突
本文作者声明以下潜在利益冲突:就业:每位作者受雇于不同的机构或组织。这些附属机构如下:MM和MS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的雇员;JRP是诺华生物医学研究公司的雇员;SS是杨森研发公司的员工;KD是百时美施贵宝的员工;CK是赛诺菲的员工;MCF受雇于Jazz Pharmaceuticals, SSM和RD是Gilead Sciences的雇员;ZY是Alnylam Pharmaceuticals的员工;PA和MH是京都麒麟制药的员工;FB是UCB的员工;JS是Pfizer Inc.的雇员。本文中的观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其各自雇主的观点、活动或政策。持股:盈利性机构聘用的作者在其所在机构持有股份。这些股份属于个人投资,不会影响研究过程、发现或本文撰写过程中的决策。作者断言,这些利益未损害研究过程和本文中所述结果的科学诚信。所有作者均参与(a)构思和设计;(b)起草条款或针对重要知识内容进行批判性修订;以及(c)将出版的版本的最终批准。根据我们的知识和信念,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都已被披露,对工作的所有资金支持在文稿中得到了适当的承认。
本文稿的作者声明如下潜在利益冲突:就业情况:每位作者均受雇于不同的机构或组织。具体隶属关系如下:MM 和 MS 为药品医疗器械管理局(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Devices Agency)员工;JRP 为诺华生物医药研究公司(Novartis Biomedical Research)员工;SS 为杨森研发公司(Janssen Research & Development)员工;KD 为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员工;CK 为赛诺菲公司(Sanofi)员工;MCF 曾受雇于Jazz Pharmaceuticals,SSM 和 RD 为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员工;ZY 为Alnylam Pharmaceuticals 员工;PA 和 MH 为Kyowa Kirin Pharmaceuticals 员工;FB 为UCB 员工;JS 为辉瑞公司(Pfizer Inc.)员工。本文稿所表达的观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其所属雇主的观点、活动或政策。股票持有情况:受雇于营利性机构的作者持有其各自雇主机构的股份。这些股份为个人投资,并不会影响本文稿的研究过程、研究结果或撰写过程中的决策。作者声明这些利益未影响研究过程的科学完整性及本文呈现的研究结果。所有作者均参与了(a)研究构思与设计;(b)文章初稿撰写或对重要学术内容进行严格修订;以及(c)最终稿件的批准。据我们所知和所信,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都已披露,对工作的所有资金支持在文稿中得到了适当的承认。
参考文献
1Sathish, J.G. et al. 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afer immunomodulatory biologics. Nat. Rev. Drug Discov. 12, 306–324
2Brennan, F.R. et al. Safety and immunotoxicity assessment of immunomodulatory monoclonal antibodies. MAbs 2, 233–255 (2010).
3Tang, Y., Li, X. & Cao, Y. Quantitatively modeling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therapeutic doses of antibodies. bioRxiv 10, 1–32 (2020).
4Leach, M.W. et al. Strategi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using a data-driven and risk-based approach in the selection of first-in-human starting dose: an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innovation and quality in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 (IQ) assessment. Clin. Pharmacol. Ther. 109, 1395–1415 (2021).
5Lebrec, H. et al. HESI/FDA workshop on immunomodulators and cancer risk assessment: Building blocks for a weight-of-evidence approach. Regul. Toxicol. Pharmacol. 75, 72–80 (2016).
6Suntharalingam, G. et al. Cytokine storm in a phase 1 trial of the anti-CD28 monoclonal antibody TGN1412. N Engl J Med 355, 1018–1028 (2006).
7Mueller, P.Y. & Brennan, F.R. Safety assessment and dose selection for first-in-human clinical trials with immunomodulatory monoclonal antibodies. Clin. Pharmacol. Ther. 85, 247–258 (2009).
8Muller, P.Y., Milton, M., Lloyd, P., Sims, J. & Brennan, F.R. The minimum anticipated biological effect level (MABEL) for selection of first human dose in clinical trials with monoclonal antibodies. Curr. Opin. Biotechnol. 20, 722–729 (2009).
9Tibbitts, J., Cavagnaro, J.A., Haller, C.A., Marafino, B., Andrews, P.A. & Sullivan, J.T.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dose selection for first-in-human clinical trials with novel biopharmaceuticals. Reg. Toxicol. Pharmcol. 58, 243–251 (2010).
10Saber, H., Gudi, R., Manning, M., Wearne, E. & Leighton, J.K. An FDA oncology analysis of immune activating products and first-in-human dose selection. Regul. Toxicol. Pharmacol. 81, 448–456 (2016).
11Saber, H., Valle, P.D., Ricks, T.K. & Leighton, J.K. An FDA oncology analysis of CD3 bispecific constructs and first-inhuman dose selection. Reg. Toxicol. Pharmcol. 90, 144–192 (2017).
12Saber, H., Thompson, M.D. & Leighton, J.K. Pharmacokinetic models for first-in-human dose selection of immune-activating products in oncology. Regul. Toxicol. Pharmacol. 149, 105616–105624 (2024).
13Janku, F. et al. Preclin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phase I study of an anti-HER2-TLR7 immune-stimulator antibody conjugate in patients with HER2+ malignancies. Cancer Immunol. Res. 10, 1441–1461 (2022).
14Davda, J.P. & Hansen, R.J. Properties of a general PK/PD model of antibody ligand interactions for therapeutic antibodies that bind to soluble endogenous targets. MAbs 2, 576–588 (2010).
15Lobo, E.D., Hansen, R.J. & Balthasar, J.P. Antibody pharmacokinetics and pharmacodynamics. J. Pharm. Sci. 93, 2645–2668 (2004).
16Stebbings, R. et al. “Cytokine storm” in the phase I trial of monoclonal antibody TGN1412: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causes to improve preclinical testing of immunotherapeutics. J. Immunol. 179, 3325–3331 (2007).
17Grimaldi, C. et al. Cytokine release: a workshop proceedings on the state-of-the-scienc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Cytokine 85, 101–108 (2016).
18Eastwood, D. et al. Monoclonal antibody TGN1412 trial failure explained by species differences in CD28 expression on CD4+ effector memory T-cells. Br. J. Pharmacol. 161, 512–526 (2010).
19Stebbings, R., Eastwood, D., Poole, S. & Thorpe, R. After TGN1412: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ytokine release assays. J. Immunotoxicol. 10, 75–82 (2013).
20Vessillier, S. et al. Cytokine release assays for the prediction of therapeutic mAb safety in first-in man trials–whole blood cytokine release assays are poorly predictive for TGN1412 cytokine storm. J. Immunol. Methods 424, 43–52 (2015).
21Frances, N. et al. Novel in vivo and in vitro pharmacokinetic/Pharmacodynamic-based human starting dose selection for Glofitamab. J. Pharm. Sci. 111, 1208–1218 (2022).
参考文献(翻译了参考文献标题)
1Sathish, J.G. et al. 开发更安全免疫调节生物制剂的挑战与方法. Nat. Rev. Drug Discov. 12, 306–324
2Brennan, F.R. et al. 免疫调节单克隆抗体的安全性与免疫毒性评估. MAbs 2, 233–255 (2010).
3Tang, Y., Li, X. & Cao, Y. 定量建模影响抗体治疗剂量的因素. bioRxiv 10, 1–32 (2020).
4Leach, M.W. et al. 采用数据驱动且基于风险的方法选择首发起始剂量的策略与建议:药物开发创新和质量国际联盟(IQ). Clin. Pharmacol. Ther. 109, 1395–1415 (2021).
5Lebrec, H. et al. HESI/FDA免疫调节剂与癌症风险评估研讨会:证据权重方法的构建模块. Regul. Toxicol. Pharmacol. 75, 72–80 (2016).
6Suntharalingam, G. et al. 抗CD28单克隆抗体TGN1412一期临床试验中的细胞因子风暴. N Engl J Med 355, 1018–1028 (2006).
7Mueller, P.Y. & Brennan, F.R. 首次用于免疫调节性单克隆抗体的人体临床试验安全性评估与剂量选择. Clin. Pharmacol. Ther. 85, 247–258 (2009).
8Muller, P.Y., Milton, M., Lloyd, P., Sims, J. & Brennan, F.R. 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中首剂人类剂量选择的最低预期生物效应水平(MABEL). Curr. Opin. Biotechnol. 20, 722–729 (2009).
9Tibbitts, J., Cavagnaro, J.A., Haller, C.A., Marafino, B., Andrews, P.A. & Sullivan, J.T. 首次人体临床试验剂量选择的实用方法. Reg. Toxicol. Pharmcol. 58, 243–251 (2010).
10Saber, H., Gudi, R., Manning, M., Wearne, E. & Leighton, J.K. FDA关于免疫激活产品及首次人体剂量选择的肿瘤学分析. Pharmacol. 81, 448–456 (2016).
11Saber, H., Valle, P.D., Ricks, T.K. & Leighton, J.K. FDA关于CD3双特异性构建体及首次人体剂量选择的肿瘤学分析. Reg. Toxicol. Pharmcol. 90, 144–192 (2017).
12Saber, H., Thompson, M.D. & Leighton, J.K. 肿瘤学中免疫激活产品首次人体剂量选择的药物代谢动力学模型. Regul. Toxicol. Pharmacol. 149, 105616–105624 (2024).
13Janku, F. et al. 针对HER2恶性肿瘤患者中抗HER2-TLR7免疫刺激抗体偶联物的临床前特性及I期临床研究. Cancer Immunol. Res. 10, 1441–1461 (2022).
14Davda, J.P. & Hansen, R.J. 治疗性抗体配体相互作用PK/PD模型的性质,适用于可溶性内源性靶点的治疗性抗体. MAbs 2, 576–588 (2010).
15Lobo, E.D., Hansen, R.J. & Balthasar, J.P. 抗体药物代谢动力学和药物效应动力学. J. Pharm. Sci. 93, 2645–2668 (2004).
16Stebbings, R. et al. 单克隆抗体TGN1412 I期试验中的“细胞因子风暴”:更好地了解原因以改善免疫治疗剂的临床前测试. J. Immunol. 179, 3325–3331 (2007).
17Grimaldi, C. et al. 细胞因子释放:关于科学现状、当前挑战及未来方向的研讨会论文集. Cytokine 85, 101–108 (2016).
18Eastwood, D. et al. CD 4+效应记忆T细胞上CD 28表达的物种差异解释单克隆抗体TGN 1412试验失败. Br. J. Pharmacol. 161, 512–526 (2010).
19Stebbings, R., Eastwood, D., Poole, S. & Thorpe, R. TGN1412之后:细胞因子释放实验的最新进展. 10, 75–82 (2013).
20Vessillier, S. et al. 用于预测治疗性单克隆抗体在首次人体试验中安全性的细胞因子释放实验——全血细胞因子释放实验对TGN1412细胞因子风暴的预测能力较差. J. Immunol. Methods 424, 43–52 (2015).
21Frances, N. et al. 基于新型体内和体外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的人体起始剂量选择——Glofitamab. J. Pharm. Sci. 111, 1208–1218 (2022).